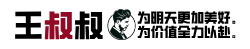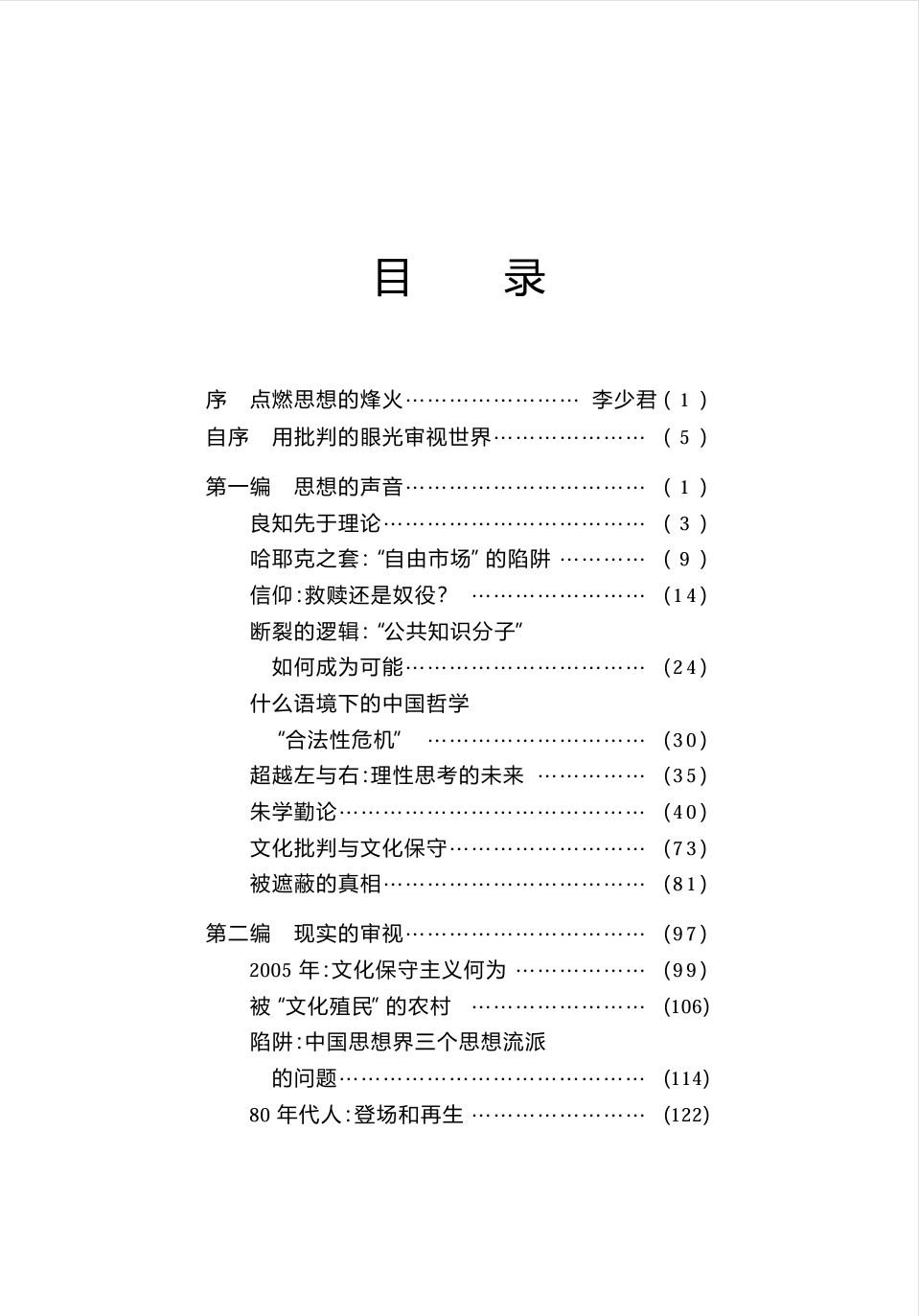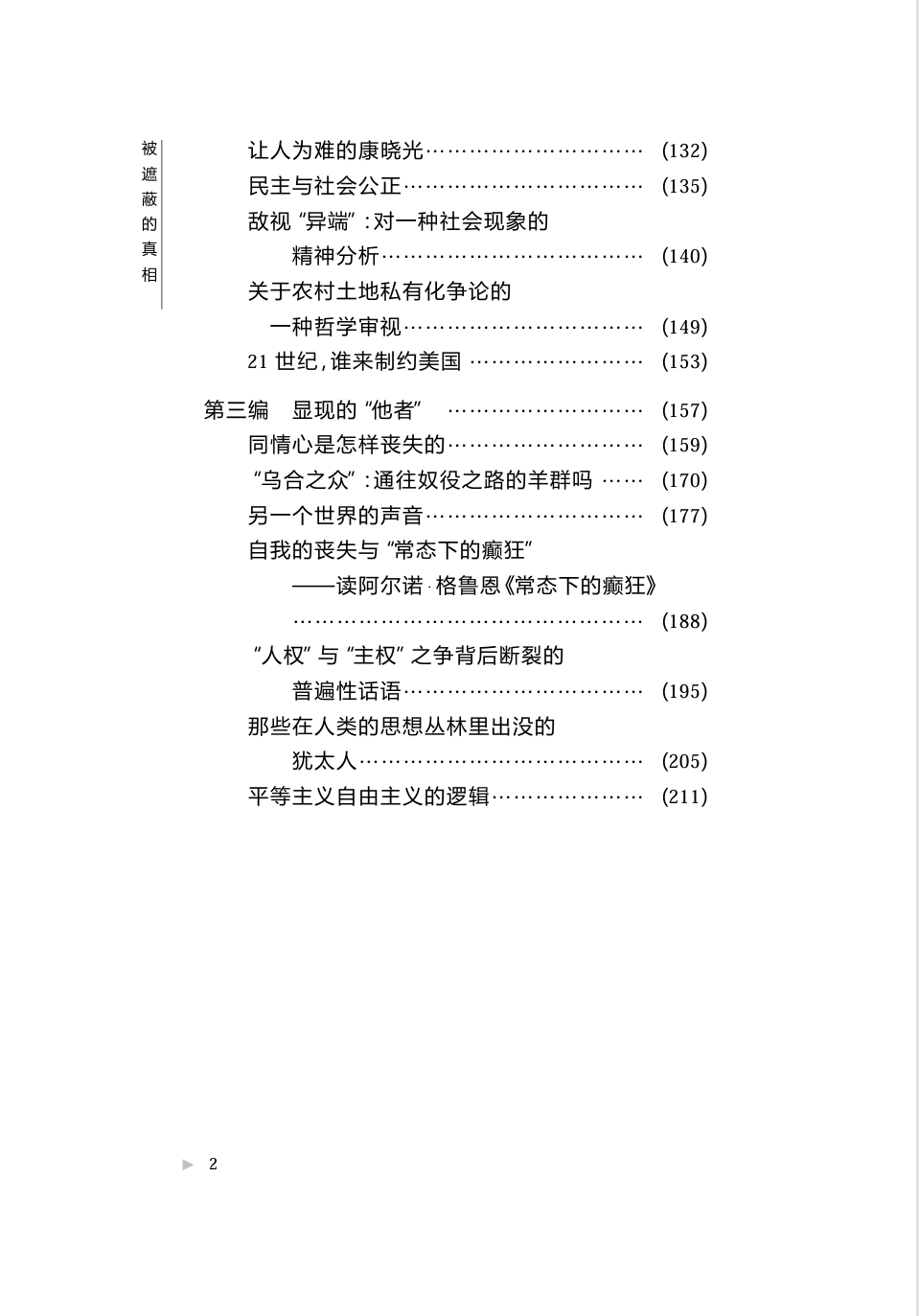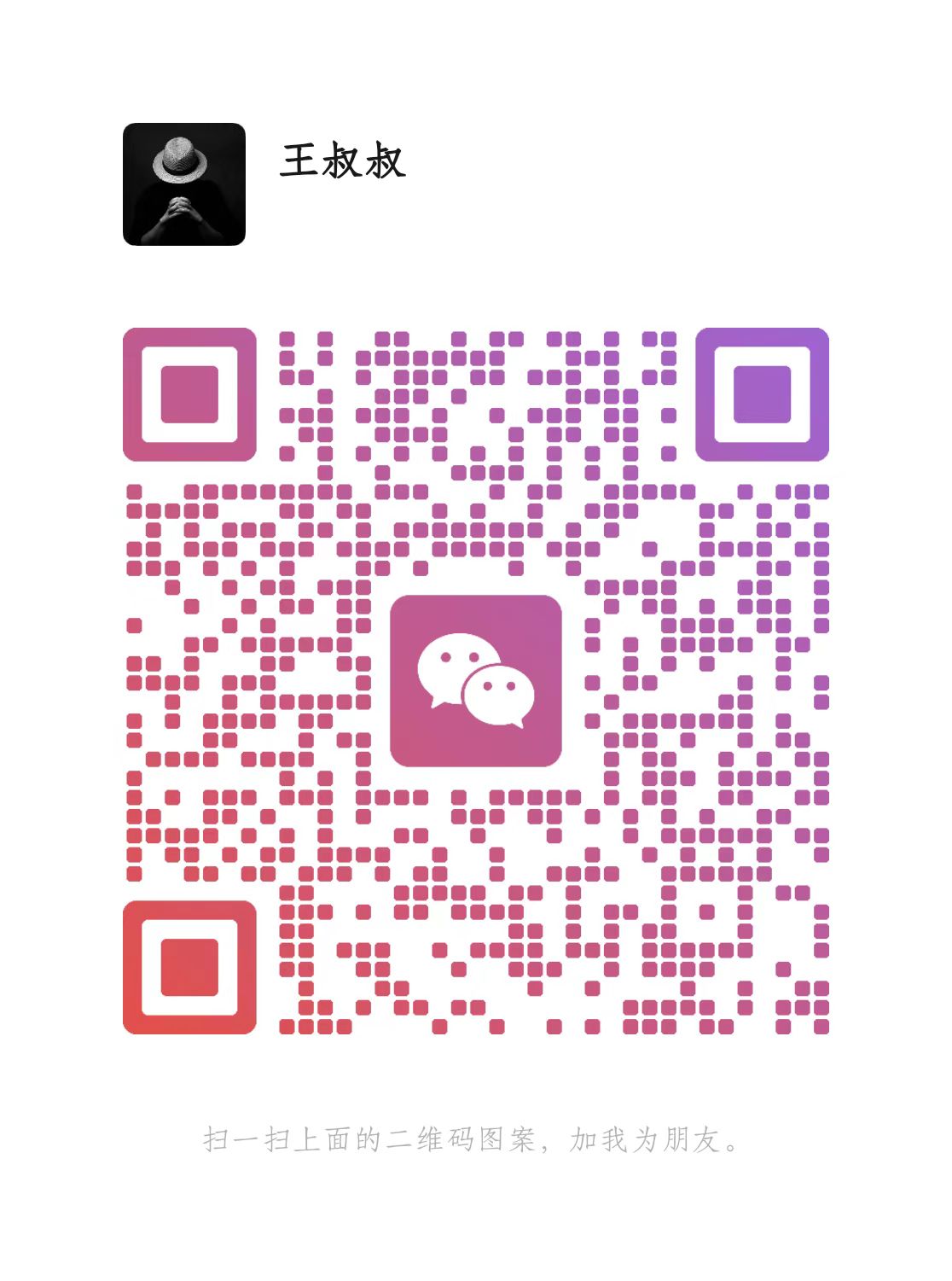作为人,我们不可能不思考,而只要追问我们思
考、选择、行动背后的逻辑、依据和环境,我们就已经
进入了“批判”的状态。而“批判”不是单纯的智力活
动,它意味着思考与行动、精神与肉体的交融,意味着
对世界真相的一种探索。它从形而下的生活状态出
发,向上盘旋,与形而上的精神理念接壤。
正因为如此,批判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,这种超
越延伸到了支撑这种现实存在的观念和法则的层面。
现实有时候在一个批判者眼里已经退化成一种载体。
观念和法则本身可以衍生出诸种形态不同的现实,但
它们在逻辑上却多具有同构性。人们无论认同还是
反对某种现实,它都可能是他们所反对或认同的观念
和法则以其内在指令渗入而衍生的一个结果。就此
而言,批判者相对于无法离开现实的社会大众来说,
注定是孤独的。
当苏格拉底衣冠不整地在大街上与人探讨什么
是正义时,他对生活的伦理内涵充满了渴望。结果他
被处死,而投票处死他的,多是那些眼神惊慌失措的
人们。克尔凯郭尔终生无法融入这个世界,在哥本哈
根阴郁的街道里,他艰难地挪动着步子。旁边是大人
们的嘲笑,背后是一群孩子的石块的追击。一直到
死,他都逃不过恐惧和颤栗的狙击。尼采在他还未疯
的时候便被视为疯子。他抱着马头痛哭的情景让我
们穿过他对平等的诅咒和对超人向往的幻象,直抵他
软弱的内心。在这一时刻还原出了一个真正的尼采:
被抛弃的只是现实的幻觉,他一直在拥抱着这个用许多幻象掩盖了的残酷的世界。
作为一条精神康复之路,精神分析显示出了无与
伦比的魅力,但“文明社会”这个“致病情境”迫使它不
得不与哲学、宗教发生联系。人的现实存在困境经过
层层追索,最终直达本体论上的存在困境。意识的分
裂使统一的世界分裂成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才能回归
和谐的各种碎片,使人与人之间异化成一种相互否定
的存在。意识的分裂、人性的恶的潜能及统治建构出
的逻辑,使哲学所论证的人的应然存在状态遥遥无
期。人的存在困境不得不指向人心和人所建构的诸
如制度、意识形态等社会工具。
因此,寻找支配现实的观念法则几乎是批判者的
“本能反应”。